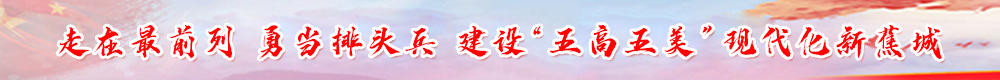当一位青年跨越十八载光阴,在十省与北京、上海二市的辽阔土地上追寻一位位牺牲烈士的足迹,他其实是在用双脚丈量民族记忆的深度;当蕉城与山西代县的抗战史研究者双手紧握,那条跨越八十多年的拯救之索终于完成最后的传递。

7月22日,在蕉城区委宣传部的会议室里,一叠史料跨越千里而来。这场特殊的会议,让抗日烈士黄家祥的革命足迹首次在闽东与山西晋北之间连成完整的轨迹。两地围绕黄家祥烈士事迹的完整性考证、精神内涵提炼及跨地域革命活动关联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互赠党史研究资料与红色文化书籍。
“黄家祥同志的故事不该被地域割裂。”抗战史研究者武凌宇将这位革命烈士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位生于1991年的青年,多年来在故乡寻访黄家祥烈士的抗日事迹,从延安一路走过他在山西省活动的各个县乡,将代县百姓口中的“黄青天”从历史尘埃中寻回。此刻,蕉城的家书与代县的故事终于交汇碰撞,放出烈士光辉的一生。
秤杆量民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出身优渥的黄家祥毅然投身抗日烽火。在遭受日寇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六步兵大队铁蹄蹂躏的山西代县,他受党的委派担任代县抗日政府司法科科长,执掌的不仅是土地、山林的纠纷裁决,更是一杆民心所向的公平秤。群众至今记得他背着干粮翻山越岭办案的身影,称他“吃苦耐劳、办事公道、毫无官架子”,“黄青天”的称号自此烙印民心。
黄家祥的生命与当地百姓水乳交融。他吃粗粮,喝冷水,主动帮群众劈柴挑水。因高度近视,黄家祥曾几次跌落山崖,群众和八路军战士屡屡用麻绳等将其救起。在敌人搜查时,群众也会帮助他伪装成哑巴、盲人,助其脱险。

因身为南方人的语言差异,黄家祥学了一年多代县方言也没有学会,群众开玩笑说他“南蛮子”“说话垮腔垮调的”,他也就笑笑。最后群众无奈,只能让他装哑巴,“你就装哑巴,敌人来围村,你就一句话不说,我们来护你。”
1940年寒冬,黄家祥身患重伤寒,被转移至繁峙县安家岭的八路军临时医院。在妇救会长秦贞茹,护理员陈大女、孟姚氏等人的救治下,他靠顽强意志战胜了死神。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成为烽火中军民鱼水情的血色见证。
1942年,黄家祥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包围,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位时年33岁的抗日战士壮烈牺牲。
步履量山河
武凌宇在代县寻访黄家祥事迹时,一位老人紧握他的手,眼中含泪:“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真好……你们若有机会,替我们看看他的家乡吧。”老人浑浊的目光中,映照出半个多世纪前那个风尘仆仆、为群众主持公道的年轻身影。
因太姥爷是当地的抗日干部,在外祖父的影响下,武凌宇从小对抗日烈士产生兴趣。上初中时,他就在县烈士陵园中的烈士塔前发下宏愿:一定要把这些烈士都找到,一定要把这些烈士的事迹都一一记录下来,让他们永续传承。自此,他开始了十八年的寻访调查研究。他走过十省二市,查阅资料、走访群众、联系亲属,致力于还原烈士事迹。

“就是因为他们是烈士,是为我们牺牲的。我通过知情人的讲述、经历者的惨痛回忆,我知道当年是一个怎么血雨腥风、黑暗暴虐的时代。”武凌宇的目光中透露着坚定,“那些烈士为我们挺身而出,将日本侵略者赶跑,迎取抗战的胜利,才有现在的我们。如果没有烈士的牺牲,或许我们就根本不会存在。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些烈士全部找到,把他们的事迹撰写出来并发表,让后来人知道我们的烈士是多么伟大。”
翻阅泛黄的档案,叩开知情者的门扉,联系散落各地的烈士亲属……十八年来,他收集了30多个关于黄家祥的珍贵故事片段,其中十余个已整理成完整篇章,发表于各类党史刊物与新闻报纸,并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上持续传播。这些文字如同点点星火,将“黄青天”的形象重新照亮。
故纸连血脉
此次蕉城之行,武凌宇携带的史料与蕉城的记载终于碰撞融合。两地围绕烈士事迹完整性考证、精神内涵提炼展开激烈讨论,明确建立长效合作机制,致力于推动史料互补与研究深化,为这位足迹跨越南北的烈士拼出更完整的人生版图。

在蔡威事迹展陈馆的肃穆氛围中,武凌宇沉静注视那些同样曾年轻炽热的生命。他深知,“黄家祥”们并非冰冷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曾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好人”。正是这份平凡中的伟大,使他们的精神在百姓口口相传中,如崖壁青松顽强生长。
山西代县群山深处,当年八路军和群众用麻绳从悬崖上救起失足跌落的黄家祥时,未必能想到,八十多年后,一位生于1991年的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将这位“黄青天”从历史迷雾中重新托举而出。

武凌宇的十八年求索非独行,是几代人用责任接力的长征。历史长河中那些被麻绳从悬崖下拉起的瞬间,终将被另一双手以笔为索,从遗忘的深渊中再次托起。
“青天”之名,从不在庙堂匾额之上,而在百姓心尖温热处。两地的接力棒交汇的这一刻,那位总摔跤的近视眼干部,终于在历史的悬崖边稳稳站定了身影。 □陈菱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