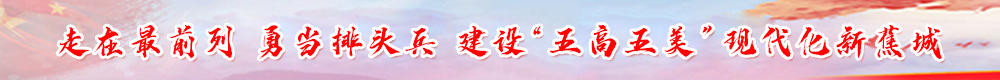陆放翁初涉宦途,足迹落于宁德白鹤峰下,领九品主簿微秩。时人戏谑七品为“芝麻”,九品之卑,几近“吏”底。其诗自谓“白鹤峰前试吏时”,一个“试”字,道尽了他与县尉朱景参这般末流小吏在权力底层踟蹰的况味。官阶虽渺如芥尘,却是书生安身立命、初探济世之道的方寸天地。陆游珍之重之,勤谨奉公。后世方志不吝赞词:明嘉靖版《宁德县志》称其“有善政,百姓戴之”;清乾隆版《福宁府志》更誉其“设施经济、体用兼备”。然则,一个羽翼未丰、权柄有限的初吏,岂能轻易翻动乾坤?史册所载其“兴利革弊,除奸惩恶”,倡茶渔,重教化,播爱国之忱,终难觅凿凿可征的煌煌功业。但这微渺的起点,烛照出一个书生胸腔内不曾冷却的炽热,那泛舟瑞安江时写下的“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岂止是对前程的期许?分明是灵魂深处不灭的星火,在宦海迷雾中执着燃烧。正是这点星火,未及一年,便引他跃离宁德,擢升福州提刑司属员(次曹)。
此后宦海浮沉,陆游力主抗金、矢志北伐的毕露锋芒,终为弥漫朝野的主和暗流所不容,直至罢归山阴故里。二十载寒暑,他荷锄垄亩,笔耕诗田。正是在这蛰居的岁月深处,一首浸润着宁德山水清芬与故友深情的诗篇悄然流淌:白鹤峰前试吏时,尉曹诗酒乐新知。伤心忽入西窗梦,同在峬村折荔枝。
放翁是青衫文吏,景参乃皂衣武尉。诗酒相酬,竟成莫逆。他们的足迹何止于峬村的荔枝林?北岭山水间亦曾回荡二人长啸。一阕《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为证: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朱景参何其有幸,两度走入陆游不朽的诗行,得以在时光长河中留姓存名。这词句以闽东风物为骨,以命运对照为脉,早已超越私人情谊的浅吟低唱。它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南宋偏安阴影下,文人灵魂深处巨大的撕扯:一面是“千岩高卧,五湖归棹”的归隐低吟,一面是“白羽腰间气何壮”的功业渴望。在理想与现实的重压下,峬村的一山一水,一枚“晚香丹荔”,竟被淬炼成承载永恒慰藉的精神故园。而那“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的殷殷叮咛,更是以最日常的物象,刻下最深沉的烙印,它是对流逝时光的抵抗,对纯粹情谊的封存。
两首诗词,同怀故人,同醉诗酒,更同寄情于那宁德的灵魂之果——荔枝。酒,这酝酿千古诗魂的琼浆,自不待言。而荔枝,自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绝唱后,又在南宋的烟雨里,被陆游于宁德“蛮江”之上,一再深情吟咏。这偏爱,岂止口腹之欲?它是对白鹤峰前、峬村林下,那段交织着青春志气与知己温情的“试吏”时光,最缠绵悱恻的回望与招魂。
言及陆游笔下的“峬村”之“峬”,《康熙字典》溯其源至《字林》,释“峬”为“好形貌”。以“峬”为名,正是取其山川形胜之美。峬村在宋代隶宁德县青田乡,明代设峬源都(亦称峬源、卓峬),清代沿袭。因其地处七都,后人多称七都峬村。此地扼福温古道支脉峬岭古道之咽喉,是交通、经济与军事的锁钥。南宋时,它作为宁德通往霍童、周墩、福安的必经之路,古道蜿蜒,连接北溪渡与八都铜镜村,构成宁德与闽北、浙南的陆路通道。峬岭垭口,烽燧兀立,警惕着海寇的窥伺;北溪渡口,帆樯如织,“一苇可航”间,盐、茶、丹荔随商旅流转。正因其枢要,陆主簿方在宁德诸多村落中独钟于此,常与朱县尉至此体察民情。
此乃职分所在,本无需如当下事事留痕。真正被陆游以文字“留痕”的,是那些触动其心魄的物事,譬如峬村的荔枝。他对荔枝的情缘,早已超越口腹。无论是宁德“峬村丹荔”的鲜甜,还是对蜀地“绿荔枝”的魂牵梦绕,这南国嘉果,已成为其诗词中凝结故土之思、友朋之谊与生命热忱的重要意象。今宁德三乐村(古峬村)仍有一株经鉴定为823年的古荔,犹自挂果。专家考其为南宋“元红”遗种,或与陆放翁当年所啖同源。诚然,陆游莅宁德距今867载,古树彼时尚未成形。然峬村宋时盛产“元红”,即陆游词中的“晚香丹荔”,品质卓绝,“丹荔垂垂映碧溪”(清知府李拔诗),部分曾为贡品,至今仍是地方风物象征,此乃不争。陆游以诗记取,力透纸背,强调此地风物在其生命记忆中的不朽印记。这不仅是味觉的存档,更是情感与历史的双重载体。两首宁德荔枝诗,如时空隧道,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伟大诗人的感官世界与精神版图。而宁德古荔的存在,则让南宋的荔枝种植史从纸页走入现实,成为陆游文化遗产中一株活着的注脚。
陆游以诗人之眼观世,所历山海风物、人情世态,皆成诗材。他摹写了霍童溪“稻垄牛行泥活活,野塘桥坏雨昏昏”的田园牧歌,也记录下三都澳“同僚飞酒海,小吏擘蚝山”的宴饮喧腾,展现闽东的丰饶与淳朴。更难得者,他以诗笔记人载事。若无陆游诗笔,朱景参这位宁德县尉,恐早已湮没于浩瀚史籍,无声无息。陆词赞其“白羽腰间气何壮”,既绘其英武之姿,更寄托了对友人建功立业的深切期许。朱县尉身为宋代县级武官,位次县令,职司缉盗治安,权责常随地方情势浮动,亦需协理赋税,与主簿陆游形成文治安民的互补。虽因史料匮乏,其生平难以详考,但在陆游的文学宇宙里,朱县尉的形象被赋予“豪壮将相”的象征意义。他们的交往,既是个人情谊的温暖纽带,更成为洞察南宋基层治理生态与士人复杂心态的一扇独特窗口。
陆游调任福州,与朱县尉天各一方,然宁德的山川草木,早已成为他们友谊的永恒见证。这份情谊,历久弥深。八十一岁高龄,放翁于梦中再见故人,夜不能寐,挥毫泣就:“伤心忽入西窗梦,同在峬村折荔枝。”此时距他宁德初仕已四十八载!近半个世纪的时空阻隔,非但未能稀释记忆,反令这追忆之痛愈加刻骨铭心。一枚荔枝,跨越生死,照见一个灵魂的重情至性。
《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以其独特的地域风物、命运映照与隐含的江湖戏谑,在陆游早期词作中卓然不群。它不仅是私人友情的丰碑,更深刻映射出南宋主和阴霾下文人普遍的精神困境,在归隐的低吟与功业的渴望间剧烈撕扯。而峬村的山水丹荔,正是在这撕扯的裂隙中,被赋予了超越时空的情感救赎力量。《予初仕为宁德县主簿而朱孝闻景参作尉情好甚》则借今昔对照、虚实相生,以极简笔墨承载了跨越时空的深情追忆。这既是陆游个人心迹的流露,亦是南宋士大夫对生命流转、世事沧桑的深沉喟叹。诗中“折荔枝”这一看似寻常的细节,因其承载的厚重情感与历史信息,已成为后世解读宋代闽地风物与士人生活情态的一把金钥。
一枚丹荔,红艳千年,它凝结的不仅是故友的欢笑与宦海的初程,更是一个时代文人的精神密码,在历史的枝头,历久弥香。 □ 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