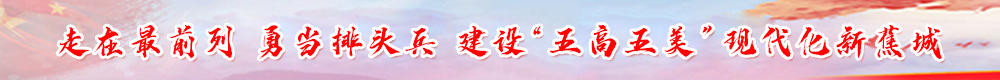我的老家在宁德古田罗源三县交界的绵延群山里,站在村里望山岭上盘旋着如螺纹般的层层茶园,它以山形地势去拥抱蓝天白云。风吹不走山村空气那抹潮湿和润滑,反而早晚时间免费地送来迷魂的白雾,把房前屋后、田地茶园、竹林树木围得水泄不通,萦绕出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再加上昼夜温差之大,这方沃野肥土也自然成了茶树最为的喜爱。
家乡茶树什么时候起栽,没有文字记载。老人口里的故事是这样流传,说是开山鼻祖从古田大甲山上下来时,挑来铺盖担子里竟带九株茶树苗,第一锄头落在这块地上时,栽的就是那些茶树苗,茶树在他们心中拿捏出多重的分量。从此,栽茶摘茶制茶的农事年年伴随着山村诞生从远古漫步走来,一碗茶的清香飘在人们清苦的劳作生活中。
我家乡人也很奇怪,好好的喝茶不叫而去叫吃茶。也许栽下第一株茶树的老祖宗是这么叫的,因而,一代传一代直到今天。咦,仔细地想想也不对,周边几十里那些比我家乡更有历史的村庄也都把喝茶叫吃茶,莫非我祖上人入乡随俗罢了。当然用家乡土话叫喝茶感觉很别扭,反而叫吃茶顺耳又好听。
小时候我在家里玩耍时,那时没通公路靠走路,每天都有邻村人打我家门口经过,有的还会上到大堂里聊天问候,长辈就拉长声叫家人:“茶汵来给人客吃。”这“汵”就是倒,一碗飘香茶水捧到客人手中。有时在村头村尾遇到过路熟人,都会客套地招呼说:“茶吃了再走。”这不仅是我村里人待客的客套,我们去周边村庄时,也享受着同等客套的待遇。
吃茶是老家那一代人源远流长风俗,代表着乡亲们热情好客的乡土文化气息,演绎厚土里深层次的人情世故。
然而,吃茶也能吃出不愉快的事来,那是临近一个村,一个炎炎夏日,年轻的风水先生匆匆赶路,路过一座破旧厝门前时,大娘看年轻人汗水涔涔,招呼他吃茶,风水先生也渴坏了也不客气。一会儿,大娘从屋里端来一大碗凉茶水给风水先生吃。风水先生接过茶碗,看到黄色的茶水上飘着稻谷壳,不禁皱起眉头,他到哪里都是享受着人家上等酒菜招待,哪有受到大娘如此不敬,怒火心中烧:“茶水里撒谷壳给我吃,这女人心太毒。”先生因太渴,慢慢吃下那碗茶,报复心也上来了,指着不远处一块地穴对大娘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接着又教大娘墓怎样做,方向怎么放,不知深浅的大娘自然是万分感激。先生见大娘深信不疑,真上了钩,满心欢喜赶路去,他心想大娘凭此把墓造了,不要几年家道败落,断了后代。
过了二十多年,上了年纪的风水先生来验证这家人,只见当年破旧房子变成三座火墙包栋的大厝,看去人丁兴旺,也是当地有钱人。先生仔细地问到他们是当年大娘后代时,迫不及待地问他们家是怎么发达起来的,主人把他奶奶当年给赶路风水先生端茶吃,风水先生送一穴墓地的事说了,还说奶奶好心肠,害怕大热天先生口干,太急吃下一碗茶可能出人命,就在碗里茶水上撒谷壳,让他慢慢吃就不会出事。先生听着像一根木桩般站立那里。
时光荏苒,老家年轻人进城打拼后,也把城里的茶文化带回村,真是与时俱进,丰富了村里吃茶文化。如堂弟去闽南参观铁观音制茶企业回来,学着闽南人做茶叶菜吃,到茶园采摘青嫩的茶叶,清洗干净后,裹上生粉浆,放入油锅炸出脆黄,摆到盘子上就是菜了,味道真好。哈哈,这真正算得上吃茶了。
我隔壁村阮蔚蕉老师现居宁德,他可谓把吃茶吃到高雅的文化艺术层次上。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小时候,他亲眼看着一些博士文人经常登门与父亲吃茶,交流文化知识。前辈们吃荼印象深刻在他幼小心灵上,以致他退休后,把全部精力花在研究中华五千年茶与诗的文化上,一个人遨游在从“荼”到“茶”,从生嚼到煮食,从药用到品味,以至于被人们赞为“灵芽”“瑞草”中。他辛勤的付出之后便是硕果累累,他编著出版了《不读诗何以解茶》《诗出有茗一福建茶诗品鉴》《茶诗里的中国韵》三本著作,同时,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相关茶与诗的文章,他把吃茶和读诗玩出如此高的文化艺术境界来,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
老家的茶园都是企业化经营了,但吃茶依然蛰伏在老家那片故土里,“吃茶,吃茶”,那是乡土韵味悠长山村人情世故中,透出的是那方水土的厚道。 □ 蔡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