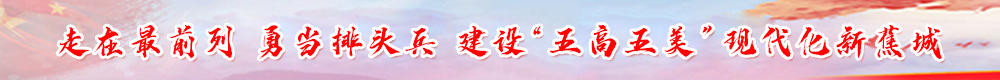鱼在中餐里大约是极为重要。过年因为期盼年年有余,所以年夜饭一定要有鱼,还不能马上就吃掉。非得等到过了除夕,真正到了春节,才被允许大快朵颐。
看陈凯歌早年拍摄的电影《黄土地》。黄土高原的百姓办喜宴,席上有一盘鱼,却是拿木头雕成的模型。远道而来采集民歌的解放军看到后错愕不已,旁边的当地人连忙解释,这不能吃,只是应个景而已。常年干旱大风的黄土高原,能吃到鱼的机会少之又少。当然黄河鲤鱼很出名,但是在汹涌澎湃的黄河里捕鲤鱼,难度不可谓不大。
宁德这边办宴席,一定也要有鱼不可。
鱼是大鱼,小鱼就显得主人家扭扭捏捏,没有待客的诚意。选什么样的大鱼,常常视季节而定。
大鱼剖开,挖去内脏,冲洗干净。在鱼背上划上数刀,为的是在腌制的时候充分入味。每次我站在旁边看厨房大师傅清理鱼肉,总想到古代的一个刑罚,“凌迟处死”,又称“千刀万剐”。把犯人割上千万刀,受尽痛苦而死。看到鱼肉从切口翻出,莫名其妙地想到这些不好的事情。
在面粉里打了鸡蛋,搅成面糊。浑身是切口的鱼已经泡在酱汁里腌透了,临下油锅前先裹一层面糊。从油锅的边缘慢慢放进一身面糊的大鱼,热油遇到大鱼,马上刺刺拉拉地闹腾起来。
我最喜欢看油炸食品的过程,突然升腾起来的油香让我欲罢不能。油炸食品又需要极度小心与大胆,要一边控制油温,也要提防食物过度油炸,好滋味尽失。另外,还要勇敢地抵抗油滴子忽从锅里飞出,溅到皮肤,一不留神就烫一个水泡。
被油滴子缠上可真是痛苦。平时炒青菜,煎鸡蛋,在需要用热油的场合,总是被油滴子攻击,皮肤迅速灼热鼓胀,一个个小水泡留在手上、胳膊上乃至脸蛋、脖颈。
大鱼在油锅里迅速变形,鱼背上的切口像绽放的花朵,一朵一朵凝结,直至最后定型。炸至两面金黄,大师傅很满意,“呸”一声吐掉叼在嘴角的香烟,拿着不锈钢漏斗,从油锅里捞出大鱼。大鱼吸饱热油,即便已经被漏斗网罗,还滴滴答答地滴着热油。
大鱼被搁置在托盘里,等着冷却后摆盘。大师傅转头继续他的工作,我凑近去看油香四溢的大鱼。
还冒着热气儿哩。伸出手,盖在大鱼上,感受到一股小小的力量带着劲儿往上窜。遇到我的手掌,四散开来,继续上升,直至消失。
被大鱼熏了一会儿的手掌油腻腻的,搓搓掌,另一手掌也被沾染。凑到鼻下嗅嗅,油香中混着淡淡的鱼腥,是不讨厌的味道。
油炸后的大鱼被摆在鱼形碟子里,就等着最后淋一道酱汁就可以上桌了。我常常在摆满大鱼的案板前驻足观看,惊叹不已,然后垂涎欲滴,恨不能据为己有。大鱼像盛开的花朵,却被人为采摘,一朵一朵安置在碟子上。
大师傅已经在熬酱汁了。通常是熬番茄汁,鲜艳耀眼。操着长柄的大铁勺,舀上大半勺番茄汁,准确无误地浇到大鱼身上。大鱼在油锅里滚了一遭,面糊迅速凝结成一层脆脆的面衣,包裹着里面柔嫩的鱼肉。淋上番茄汁后,面衣自发自觉地拼命吮吸。有时候淋的少了,回头发现汁儿几乎被吸干,再淋半勺。
手艺好的师傅可以保证即便面衣吸饱番茄汁,也不会浸润到里面的鱼肉。
淋了番茄汁,赶紧上桌。筷子伸向大鱼,夹住蜷曲挺立的鱼肉,用力一扭,一块鱼肉被扯下,露出面衣下洁白滑嫩的鱼肉。有的人喜欢蘸点儿番茄汁再入口,也有的扯下鱼肉后就开吃。
面衣的酥脆,鱼肉的柔软,加上酸甜的番茄汁,博得老少的欢心。大鱼常常是宴席上最受喜爱的菜肴之一。味道好,主家和厨师都受到夸赞。
吃剩的大鱼带回家,回锅煮了,面衣柔软,鱼肉更甚,入口又是一番新的味觉享受。
不浇番茄汁的大鱼也很好吃。因为已经充分腌制才下锅油炸,所以吃起来就像是吃油炸小零食一般,松脆,咸鲜,欲罢不能。
可是,现在的宴席为了赶速度,省成本,利用冷冻鱼来做这道菜,风味已经失了几分。加上厨师功力尚浅,吝啬用油,又选用罐头番茄汁,入口是满嘴的防腐剂味道。
这哪里是吃鱼呢。 □ 吕玉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