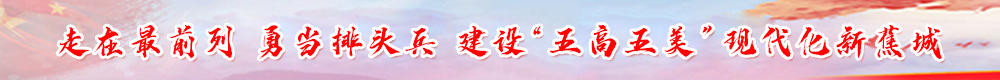童年的甜味总是被时光吐出糖丝与冬日凛冽的寒风缠绕,当中最绵长的那一丝那一缕,始终藏在母亲熬出的金黄色蕃薯糖烟火里。想着人生几十年犹如白驹过隙,唯独只有那丝丝缕缕的甜,像站立村头几棵风水树的老根般深深扎进记忆泥土里,在静静的岁月风霜里愈发清晰,默默支撑着往后每一个坎坷需要温暖的瞬间。
年底了,每当那股强劲的西伯利亚寒风掠过家里木条钉的窗棂时,那一股潜伏一年的甜味似乎随风而来,又会顺着血管荡漾奔流,将沉淀已久的思绪拽回我那个偏僻的老家——罗源县乡下那一个将至暮年的老灶台边。
蕃薯糖,顾名思义是以蕃薯作为灵魂凝固的生命。老家地处闽东群山的褶皱里,重峦叠嶂造成水田稀缺,旱地自然就多了起来,蕃薯园自然也多,它是顺着山势成片成片铺展开的。蕃薯生性耐旱,正好成了它生根长个的乐土。
秋风把山里的野柿捂得黄眯眯之后,乡亲们见到了季节来临,将园里的蕃薯挖回家,把饱满的大蕃薯切成丝,晒干了叫蕃薯米,充当下年的口粮。那些个头小又晒不了蕃薯米的蕃薯,反倒是“宝贝”被小心放到屋角里,别瞧它模样不起眼,经月余静置沥干,水分慢慢蒸发,糖分却在薯肉里悄悄凝聚,等窗外霜雪落地起白时,便成了熬糖的最佳原料。
熬糖前几日,母亲总要先养一盆麦芽。这麦芽是熬蕃薯糖的“糖灵”,堪比中药里画龙点睛的药引。她把颗粒饱满的麦粒用温水浸得发胀,倒在铺了棉布的竹篮里,再盖上厚棉被保温。此后每日清晨,母亲都会掀开棉被查看,用手指轻轻拂过麦粒。待嫩白的芽尖像害羞的春草般冒出头,越长越像细细的豆芽菜时,母亲便高兴地笑着说:“可以熬糖啦。”
这时村里家家户户像听了季节的哨音般都在熬蕃薯糖,他们的灶膛都亮着光,跳跃的火苗映着窗纸,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薯香与麦芽香,整个村子都在酝酿一场冬天寒冷的甜蜜。
熬蕃薯糖看着简单,实则是场费心的“慢功夫”。清晨吃过稀粥,母亲便叫我们从屋角搬出蕃薯,坐在水井边仔细挑选,烂了的扔进喂猪的木桶里,稍大些的切成小块,连同小蕃薯一起倒进那口黑黝黝的大铁锅。清水要没过薯块,母亲坐在灶椅上添上柴火,灶膛里立刻腾起红红火火的火苗,舔着乌云般的锅底“噼啪”作响。不多时,锅里便冒出丝丝缕缕的白气,先是淡淡的薯香,渐渐变得浓郁香甜,钻得满屋子都是味道。我咽几口口水,忍不住围着灶台转,见母亲掀起锅盖腾起白汽时,就伸手扯母亲的衣角:“娘,我饿了,想吃蕃薯。”拿起一根筷子插进蕃薯中间去,拿起来像糖葫芦那样蕃薯串递给我,并说:“小心烫到。”我等不了蕃薯凉去,迫不及待边呵气边吃,烫热的薯肉咬在嘴里,比刚挖出来时甜上好几倍,软糯里还带着一股清润的香。
蕃薯在锅里煮上三四个小时,慢慢地变得软烂如泥时,母亲便把先前养好的麦芽倒进去,搅拌均匀继续煮。直到薯泥与麦芽彻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浅黄色的汤汁,母亲退出灶膛里柴火后,拿来一块粗纱布,四角系在木架上,架在灶台边的一个大木桶上方。她用一把长勺子将锅里的薯泥一勺勺舀到纱布上,像过滤豆浆那样过滤蕃薯汤汁,汤汁下去慢了,母亲双手攥着纱布两端用力挤压,烫得不时把手缩回放到嘴巴前吹气,浅黄的薯汁便顺着纱布缝隙缓缓滴进木桶,这便是蕃薯糖的“胚胎”,是甜味最初的模样。
最关键的熬制环节,要从午后一直持续到深夜。母亲把木桶里的蕃薯汁又倒回铁锅,灶膛里重新添上柴火,这次火候掌握得有度,火不能太旺,防止糊底,也不能太弱,弱了水分蒸发太慢。
母亲见锅里蕃薯汁少了,又把木桶里蕃薯汁舀到锅里去熬,如此往来几次要熬到鸡叫头遍。兄弟姐妹们熬不住长困,早早就钻进被窝,我想吃蕃薯糖执着地坐在灶膛前,一边盯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一边望着灶台上袅袅升起的白气,总觉得时间走得比蜗牛还慢。
母亲最懂我的心思,见我坐得发蔫,便用小碗盛半碗浓稠的蕃薯汁递给我:“吃了,就去睡觉。”我喝完了,觉得那蕃薯汁甜得清淡,虽然没有我味蕾里储存的那味道,但也足以让我提振精神,没了睡意。
熬蕃薯时间,是乡下天气最寒冷的。那时我穿的衣服单薄,坐在灶膛前,前面火烤得燥热,脸上红扑扑的,背后穿膛寒风“嗖嗖”地往衣服缝里钻,冻得背上如刀削般疼痛。
灶火还在烧,锅里热气一团一团往屋顶腾起,母亲拿一把椅子坐在锅旁,看着锅里的蕃薯糖,又暖身体。我坚持不住了,困意涌上来,闭上眼,头像鸡啄米般点着,几次差点栽倒地上,都是母亲眼疾手快把我拽住,母亲愠怒说:“叫你又不去睡,留着明天给你吃,又不会给人偷吃了。”为了能吃到蕃薯糖,我又硬生生睁大眼睛说:“我又不困啊。”母亲反驳道“不困,没拉你几把,你头就磕到地上石头了。”
母亲看我这般模样,心里又痛又着急,可锅里慢悠悠的糖水,似乎跟我们跑马拉松比赛般,让你催不了又急不得。我断断续续几次站在锅边,看锅里糖水翻着白浪腾起白雾,母亲时不时拿起一根竹筷,伸进锅里蘸一下薯汁,快速举到昏黄的煤油灯前。灯光晃荡中,竹筷上的薯汁像小水珠似的往下滴,母亲对着竹筷自言自语:“这么久了,还没拿旗。” 我那时不知道“拿旗”的意思,后来才知道,“拿旗” 是家乡熬蕃薯糖的行话,等薯汁熬得足够浓稠,用筷子蘸起时,糖汁会像一面小旗子似的挂在筷尖,欲滴未滴,这才是蕃薯糖熬好的信号。
不知道熬到了半夜几点,我伏在长条椅上迷迷糊糊快睡着时,忽然听见母亲惊喜的喊声:“拿旗了。拿旗了。”我像被施了魔法似的,瞬间清醒过来,一骨碌爬起来凑到灶台边。看见锅里糖汁稠了冒着气泡,又见母亲手里的竹筷上,挂着一缕琥珀色的糖汁,真的像一面小小的旗帜,在煤油下泛着温润的光。那一刻我心里的欢喜,像战场上战士把红旗插上阵地的胜利喜悦。蜡黄的灯光照着母亲脸上露出满是成就感,她见我急了就说:“再等一会儿,火候还差一点。”她俯下身,把灶膛里冒白烟的柴块夹出来,只留下通红的炭火,这样既能慢慢蒸发余水,又不会把糖烤焦,是老一辈人传下的“火候经”。
终于起锅了。母亲先用竹筷在锅里卷了一圈,卷出一串像糖葫芦似的糖丝递给我。我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甜丝丝的糖在舌尖化开,带着浓浓的薯香。等母亲把浓稠的蕃薯糖舀进瓷瓮,我又盯着锅底的糖锅巴不放,母亲明白我的意思用锅铲铲出几块,金黄色的糖锅巴脆生生的,咬一口“咯吱”响,甜里裹着焦香,那滋味,真是让童年的时光都变得格外香甜。
在老家,蕃薯糖不仅孩子们爱吃,而且灶神也喜爱,是送灶神“重头戏”供品重要原料之一。每到腊月送灶神前几天,母亲就会用蕃薯糖做糖豆,先把大米炒熟磨成粉,再磨一小碗黄豆粉,把瓷瓮里的蕃薯糖倒进锅里煮开,然后把米粉和黄豆粉一起倒进去快速搅拌,等混合物变得黏糊糊的,就铲起来倒在铺了一层白色米粉的簸箕上,趁着温热,母亲把它搓成细细的长条,再掐成小指头般大的糖豆。刚做好的糖豆软乎乎的,甜得润口,不过放几天就变硬了,幸好我那时牙口好,再硬也能咬得津津有味。村里家境好些的人家,会在米粉里加些糯米粉,这样糖豆放久了也不容易硬,也有少数人家还会加些花生仁,那在当时可是难得的“奢侈品”。
送灶神那天,灶台上摆上一盘裹着白色粉末的糖豆,又有水果和红酒,在蜡烛的光亮中默默数着过去时间,人们都说灶神吃了糖豆,因甜了嘴,到了天庭不会说东家的坏话。供完灶神,邻居们就会互相串门,你尝尝我家的糖豆,我品品你家的糖豆,欢声笑语里,年味也渐渐浓了起来。
如今,老家的乡亲们大多搬进了城里生活,剩下老人守候村庄,种的蕃薯少了,偶尔榨些蕃薯粉,没有人去熬蕃薯糖。我早年离开家乡外出谋生,父母亲也相继离世,熬蕃薯糖的美好时光,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过往。每当冬日寒风起时,吹起我心中的波澜,总会想起那口至今还被我保护的老灶台,想起那跳动的灶火,还有母亲举着竹筷喊 “拿旗了”的模样。
我时刻盼着,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回到乡下,在老家的院子里种一畦蕃薯,等冬天来了,像母亲当年那样,坐在老灶台,生起红红的灶火,熬一锅香甜的蕃薯糖,再做些糖豆,送灶神时,把那些城里买的、味道寡淡的灶糖灶饼换下来,让灶神尝尝久违的,而又属于家乡那种带着烟火气的糖豆。 □ 蔡光